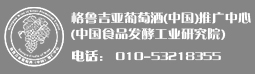行业新闻
《华尔街日报》:格鲁吉亚是否将成为下一个葡萄酒大国?
作者:文/ 塔拉·伊莎贝拉·伯顿 发布时间:2016-05-01 关注度:60
格鲁吉亚卡赫基省坐落于高加索山麓,以风光旖旎的小镇,田园诗般的乡村和源远流长的酿酒传统而著称,而今,卡赫基正展现出她醉人的风姿。
早上9:30分,我已经微微有些醉意。纳帕雷利位于卡赫基省,唯一的路两旁点缀着石头房屋和茂盛的石榴树,在这座村庄的“双子老酒庄旅馆”,早餐时间可以品尝无限量的葡萄酒。对于热情洋溢的旅馆经理艾尔达·拉米什维利,“品尝”意味着满满三杯葡萄酒。
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山麓,黑海之滨,在这座后苏维埃时期的小国旅行是对酒精代谢能力的一场考验。任何一位外国游客只要静静地坐上一会儿,便会有人习惯性地劝酒——无论是葡萄酒,白兰地或是恰恰——自家在葡萄汁中混入葡萄皮酿制的烈酒,具有杜松子酒的风味。但据当地人表示,在葡萄酒的发源地,格鲁吉亚葡萄酒主要产区卡赫基,喝酒才是正经事。
从好的方面来看,当地人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无需担心宿醉。格鲁吉亚人认为用传统的qvevri陶罐(容量为1000升,以蜂蜡密封并埋入土中的陶罐)酿制的葡萄酒不会导致宿醉。“这是格鲁吉亚传统工艺。”拉米什维利先生解释道,向我展示酒庄地上排成一列的一百只qvevri陶罐。而“欧洲工艺”发酵的葡萄酒(在罐中发酵,移至橡木桶中熟成)则“轻飘飘的,只能作为开胃酒。”他有些不屑地抽了下鼻子。Qvevri陶罐白葡萄酒风格尖锐,口味浓烈,由于吸收陶土中的色素而呈琥珀色调,而陶罐红葡萄酒则颜色深沉浓郁,甚至有shavi gvino(黑葡萄酒)之称。
几千年来(最早的qvevri陶罐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卡赫基的酿酒业一直以家庭为单位。即使是现在,我遇见的每一个卡赫基人几乎都以自家后院的qvevri陶罐为荣。距离60英里以外,居住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亲戚仍然会在周末带着五加仑的塑料罐,在姑姑家的后院灌满葡萄酒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但在卡赫基,酿酒正从家族趣味逐渐转向商业行为。过去五年中,旅游业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这个风光如画的产区未来将成为黑海之滨的勃艮第。格鲁吉亚的低地与法国南部在气温和降水量上颇为相似,而卡赫基的铁锈色泥土更使产自该地区的葡萄酒呈现一丝泥土般的暗色。
“许多格鲁吉亚葡萄酒或许缺乏现代技术带来的复杂层次。”美食和葡萄酒专业作家卡拉·卡帕博说,但最好的是,“qvevri陶罐葡萄酒以最纯净的方式呈现出葡萄的自然风味,没有橡木桶或其他工艺带来的层次感。”
“双子老酒庄”是一座房梁用木头建成,结构稍显杂乱的石头建筑,每个房间都用羊皮壁毯装饰,这里有一座新建成的葡萄酒博物馆,一家礼品店和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农民蜡像。数英里之外,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优雅的极简风格建筑——舒曼酒庄,这座德资酒庄同时经营旅馆业务,可承办正式品酒会和生产设施参观活动。“2004年,格鲁吉亚仅仅接待了120,000名外国游客,”舒曼酒庄经理伊利亚·达图纳什维利说:“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六百万。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人们都满怀工作的热情和动力。”达图纳什维利先生接下来解释道,这种热情部分是因为格鲁吉亚希望脱离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俄罗斯是格鲁吉亚葡萄酒最大的进口国,最近却在政治上与格鲁吉亚为敌。(斯大林是格鲁吉亚葡萄酒的忠实拥趸,曾以铁路运输大量葡萄酒,跨越整个高加索地区。)和格鲁吉亚许多其他大型酿酒厂一样,舒曼酒庄将重点放在来自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客上。
亲自造访的每一座葡萄园都洋溢着乐观和活力,在呈现折中主义风格的梅尔酒庄(Chateau Mere)——这座酿酒厂同时是一家度假村——熊皮地毯装饰的旁边是大卫·鲍伊,伊丽莎白·泰勒的照片,快活的老板季加一边嘲笑我的沙拉晚餐(“你是胡萝卜吗!”),一边为我端上大碗庄的新鲜黑莓。从此处驱车一小时,便来到了意大利风情的西纳基,这里,19世纪如彩色粉笔画一般的房屋于2007年经过修缮,竟然透着一丝不可思议的神秘感。这里,美资酒庄“山鸡之泪”的职员操着流利的英文,邀请观光客品鉴美酒并跃身上马,开始一段葡萄园之旅。
在酒庄之外的地方,卡赫基展现出一派喧闹而生机勃勃的景象。某个午后,我一边散步,一边寻找省内一座历史长达数世纪的修道院。唯一一条省级公路两旁是核桃树和形状古怪,苏维埃时期的二战纪念碑。一袭黑衣的妇人沿街销售自家产的蜂蜜,无人放牧的乳牛阻塞着交通。我发现自己迷失在一片到处是蝴蝶的密林中,偶遇一位老者怀抱一大捧新鲜采撷的蘑菇,他坚持说自己知道方向。而事实上他对我的目的地一无所知,我继续向前走,注意到一堵爬满青苔的墙后面矗立着一座中世纪小教堂,空无一人,连一块匾额都没有,只有嗡嗡嘤嘤的蜜蜂久久盘旋。
在卡赫基的最后一天,我信步于卡赫基省会城市特拉维一座带有遮阳蓬的集市,路边的妇女头戴方巾,叫卖着新鲜粉红的番茄,男人们用可乐瓶装着自家酿造的qvevri陶罐葡萄酒,以80分一瓶出售,配上附近山区出产的山羊乳酪。两个老人朝我喊“是游客吗?”“要恰恰蒸馏酒吗?”他们为我斟了一杯酒,以格鲁吉亚的礼节祝酒:“为新朋友干杯,为爱干杯,为格鲁吉亚干杯!”
早上9:30分,我已经微微有些醉意。纳帕雷利位于卡赫基省,唯一的路两旁点缀着石头房屋和茂盛的石榴树,在这座村庄的“双子老酒庄旅馆”,早餐时间可以品尝无限量的葡萄酒。对于热情洋溢的旅馆经理艾尔达·拉米什维利,“品尝”意味着满满三杯葡萄酒。
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山麓,黑海之滨,在这座后苏维埃时期的小国旅行是对酒精代谢能力的一场考验。任何一位外国游客只要静静地坐上一会儿,便会有人习惯性地劝酒——无论是葡萄酒,白兰地或是恰恰——自家在葡萄汁中混入葡萄皮酿制的烈酒,具有杜松子酒的风味。但据当地人表示,在葡萄酒的发源地,格鲁吉亚葡萄酒主要产区卡赫基,喝酒才是正经事。
从好的方面来看,当地人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无需担心宿醉。格鲁吉亚人认为用传统的qvevri陶罐(容量为1000升,以蜂蜡密封并埋入土中的陶罐)酿制的葡萄酒不会导致宿醉。“这是格鲁吉亚传统工艺。”拉米什维利先生解释道,向我展示酒庄地上排成一列的一百只qvevri陶罐。而“欧洲工艺”发酵的葡萄酒(在罐中发酵,移至橡木桶中熟成)则“轻飘飘的,只能作为开胃酒。”他有些不屑地抽了下鼻子。Qvevri陶罐白葡萄酒风格尖锐,口味浓烈,由于吸收陶土中的色素而呈琥珀色调,而陶罐红葡萄酒则颜色深沉浓郁,甚至有shavi gvino(黑葡萄酒)之称。
几千年来(最早的qvevri陶罐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卡赫基的酿酒业一直以家庭为单位。即使是现在,我遇见的每一个卡赫基人几乎都以自家后院的qvevri陶罐为荣。距离60英里以外,居住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亲戚仍然会在周末带着五加仑的塑料罐,在姑姑家的后院灌满葡萄酒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但在卡赫基,酿酒正从家族趣味逐渐转向商业行为。过去五年中,旅游业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这个风光如画的产区未来将成为黑海之滨的勃艮第。格鲁吉亚的低地与法国南部在气温和降水量上颇为相似,而卡赫基的铁锈色泥土更使产自该地区的葡萄酒呈现一丝泥土般的暗色。
“许多格鲁吉亚葡萄酒或许缺乏现代技术带来的复杂层次。”美食和葡萄酒专业作家卡拉·卡帕博说,但最好的是,“qvevri陶罐葡萄酒以最纯净的方式呈现出葡萄的自然风味,没有橡木桶或其他工艺带来的层次感。”
“双子老酒庄”是一座房梁用木头建成,结构稍显杂乱的石头建筑,每个房间都用羊皮壁毯装饰,这里有一座新建成的葡萄酒博物馆,一家礼品店和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农民蜡像。数英里之外,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优雅的极简风格建筑——舒曼酒庄,这座德资酒庄同时经营旅馆业务,可承办正式品酒会和生产设施参观活动。“2004年,格鲁吉亚仅仅接待了120,000名外国游客,”舒曼酒庄经理伊利亚·达图纳什维利说:“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六百万。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人们都满怀工作的热情和动力。”达图纳什维利先生接下来解释道,这种热情部分是因为格鲁吉亚希望脱离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俄罗斯是格鲁吉亚葡萄酒最大的进口国,最近却在政治上与格鲁吉亚为敌。(斯大林是格鲁吉亚葡萄酒的忠实拥趸,曾以铁路运输大量葡萄酒,跨越整个高加索地区。)和格鲁吉亚许多其他大型酿酒厂一样,舒曼酒庄将重点放在来自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客上。
亲自造访的每一座葡萄园都洋溢着乐观和活力,在呈现折中主义风格的梅尔酒庄(Chateau Mere)——这座酿酒厂同时是一家度假村——熊皮地毯装饰的旁边是大卫·鲍伊,伊丽莎白·泰勒的照片,快活的老板季加一边嘲笑我的沙拉晚餐(“你是胡萝卜吗!”),一边为我端上大碗庄的新鲜黑莓。从此处驱车一小时,便来到了意大利风情的西纳基,这里,19世纪如彩色粉笔画一般的房屋于2007年经过修缮,竟然透着一丝不可思议的神秘感。这里,美资酒庄“山鸡之泪”的职员操着流利的英文,邀请观光客品鉴美酒并跃身上马,开始一段葡萄园之旅。
在酒庄之外的地方,卡赫基展现出一派喧闹而生机勃勃的景象。某个午后,我一边散步,一边寻找省内一座历史长达数世纪的修道院。唯一一条省级公路两旁是核桃树和形状古怪,苏维埃时期的二战纪念碑。一袭黑衣的妇人沿街销售自家产的蜂蜜,无人放牧的乳牛阻塞着交通。我发现自己迷失在一片到处是蝴蝶的密林中,偶遇一位老者怀抱一大捧新鲜采撷的蘑菇,他坚持说自己知道方向。而事实上他对我的目的地一无所知,我继续向前走,注意到一堵爬满青苔的墙后面矗立着一座中世纪小教堂,空无一人,连一块匾额都没有,只有嗡嗡嘤嘤的蜜蜂久久盘旋。
在卡赫基的最后一天,我信步于卡赫基省会城市特拉维一座带有遮阳蓬的集市,路边的妇女头戴方巾,叫卖着新鲜粉红的番茄,男人们用可乐瓶装着自家酿造的qvevri陶罐葡萄酒,以80分一瓶出售,配上附近山区出产的山羊乳酪。两个老人朝我喊“是游客吗?”“要恰恰蒸馏酒吗?”他们为我斟了一杯酒,以格鲁吉亚的礼节祝酒:“为新朋友干杯,为爱干杯,为格鲁吉亚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