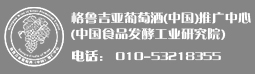作者:朱利安·阿拉森 发布时间:2015-07-02 关注度:296
当海鸥牌汽车风驰电掣般穿过第比利斯蜿蜒的鹅卵石街道,市场摊贩和骑车的人们纷纷闪避,我坐在这辆老式轿车的后排座位上,那个原本属于第一书记的位置宽敞得简直可以容纳一群干部开会。苏联政委们已不复存在,但俄罗斯挥之不去的阴影仍然如浮雕一般刻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豪华酒店般气势轩昂的海鸥牌汽车呼啸着,仿佛在宣告那段格鲁吉亚人努力忘却的历史。
在高加索山脉的背风处是欧洲与中亚的分界线,北面是战火频仍的俄罗斯联邦自治共和国,例如车臣和达吉斯坦;西面遥望黑海和土耳其,东临阿塞拜疆,南濒亚美尼亚。第比利斯自公元前200年便是其后演化为丝绸之路的商路上一座重要驿站。这座布满冰川和肥沃谷地的国家于公元4世纪基督教化,境内有150个民族,目前亟需开发——随着国家逐渐摆脱独立之初的混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几座颇具现代感的高级酒店)逐步到位,这一趋势堪称前所未有。
抛开比比皆是的欧洲风情和合乎21世纪潮流的发展状况不谈,洞穴堡垒,牛仔,佩剑吟诗的山人,遁世独居的隐者和坐在马车上,眉眼如小鹿般娇俏的女子让格鲁吉亚的神秘魅力丝毫不减。这里是约二万五千条河流的故乡,猞猁,狼和熊在河岸上逡巡。探索这多姿多彩的秘境不亚于一场启迪灵魂之旅,但旅行者的选择却仍然有限:或是按照标准行程单独旅行,或是参加有导游陪同的旅行团,或是——当然是更符合发展潮流的选择——根据兴趣定制专属行程。现居美国的格鲁吉亚专家克尔和唐尼详细叙述了前往博物馆和城堡的特殊路线,知名音乐家的私人演出和热门旅行线路之外的庄园邀请函。“赴格鲁吉亚旅行如同儿时的梦想成真,亲眼目睹中世纪城堡坐落在天堂般的群山之中。”大卫·琼斯说:“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这样不加雕琢的原生态。”
然而在第比利斯,积雪覆盖的山峰虽宛然可见,但毕竟与气氛轻快的咖啡馆和首都拜占庭式的风姿隔开了一段距离。美轮美奂的奥斯曼式建筑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故居,而林荫大道两旁则矗立着歌剧院,原生艺术风格的议会大楼和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博物馆中收藏着大量公元前3世纪的金首饰,而四楼的展厅则震撼着参观者的内心:以苏联占领为主题的展览讲述了那段压迫史,并以视频脚本记录了2008年的袭击。自从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从格鲁吉亚分裂以来——这两个地区目前仍被叛军控制并且很可能持续——格鲁吉亚与之前的殖民国关系降到冰点,两国断交,俄罗斯下令禁止格鲁吉亚公民入境。
然而,当美食爱好者坐在安巴萨多里餐厅,俯瞰着将首都一分为二的穆赫瓦里河美景,面对气味浓烈的山羊乳酪“哈贾普里”(格鲁吉亚版的披萨饼)大快朵颐时,这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从一些人红扑扑的面色可以看出,他们刚刚在有着巨大穹顶的奥贝里阿尼浴场痛快地搓了个澡,而格里沙什维利街上,广受好评的现代风格波西玛餐厅旁边,宾客们可以在刚刚翻修过,历史悠久的硫磺浴场内尽情放松,享受轻柔的按摩而不是猛力的搓洗。眺望上方,古城仿佛从气势恢宏的卡特里斯·德达城堡处沿山而下,姜饼色的阳台以诡异的角度从尚在修葺的旧屋舍中旁逸斜出。
从市区一路向北,便是古老的格鲁吉亚军队公路,这里,驾车仿佛被赋予了情感疗愈的功效,这一点仅次于Khridoli(格鲁吉亚式自由搏击)。对于一个曾八次被帖木儿率军攻入,又被成吉思汗觊觎,命途多舛的国家,格鲁吉亚人善于顺应时代精神。权威的《Bradt旅游指南》作者蒂姆·布尔福德在书中提及格鲁吉亚人时,称他们“享受着生活和美酒,翩翩起舞般穿过历史的长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不久便在军队公路上高耸的悬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穆赫瓦里河与阿拉格维河交汇之处,巍然耸立着6世纪修建的杰瓦里修道院,尽管蜜糖色的外观饱受狂风侵袭,但这座圣所仍是宁静的港湾,映在烛光和由穹顶倾泻而下的日光中。一位隐居此处的修士每日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守护着这座修道院。
修道院下面是格鲁吉亚的灵魂,也是昔日的首都斯凯塔城(Mtskheta),目前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置身于中世纪斯维迪霍维利(Svetitskhoveli)大教堂中,我仿佛被钉在17世纪基督复活的壁画中,壁画上有两只水母——或是两架飞碟,我向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此行的向导梅拉·考巴西泽提出了疑问,一通格鲁吉亚语从与我腰部齐平的高度甩来,身材矮小的修士看起来怒发冲冠。“是太阳和月亮,不是什么碟子!”考巴西泽教授翻译道。我们连忙道歉,在被当成传播异端邪说的同谋犯而遭受驱逐前匆匆离去。在不远处的桑塔沃(Samtavro)修女院中,朝圣者们亲吻着玻璃棺,里面长眠着在克格勃手下殉道的圣加百列永不朽坏的身体。“他至死都在为那些凌虐他的人的灵魂祷告。”一位修女说。
汽车前行一个小时便到达了戈里,这座城市以斯大林的故乡而著称,当地专门修建了一座博物馆纪念这位将军的诞生。然而在这座布置着丰富展品和照片的博物馆中,然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或是在劳改营和饥荒中死去的五百万人。阴郁的大厅内满是上了年纪,靠养老金过活的当地人,或许他们是这位前苏维埃领导人在格鲁吉亚最后的拥戴者(可以说是后无来者,毕竟斯大林对自己故乡的残暴程度和对待前苏联其他地区毫无二致,他甚至连自己母亲的葬礼都未参加——在格鲁吉亚人眼中,这无异于赤裸裸的侮辱)。即使是在戈里,人们对斯大林的热情在2008年8月的冲突中随着俄罗斯轰炸公寓,占领城市而渐趋消退。毫发无损的惟有铁道上的装甲车厢,众所周知,恐惧飞行的斯大林一直乘这节火车出行。车厢旁边是斯大林出生的房子,如今包裹在一座玻璃屋顶的建筑物中,乍看上去如同乐购连锁超市(由于没有暖气,即使是老年人中也无人问津)。
我们继续前行,在琼斯熟识的当地合作伙伴名下的古堡中享用了午餐。这座位于山地小镇西纳基附近的古堡是斯万尼泽家的夏季避暑地。当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对游客而言还是禁地时,这个家族为格鲁吉亚向西方游客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伴着在烤架上转着圈的猪肉串和室外管式烤箱中烘焙的面包,其他的宾客被逐一介绍:古拉米,尼可和比茨纳身穿传统的红色斗篷,腰佩短剑,手持panduri(一种类似古琵琶的当地乐器)。以务农为生的他们是著名的古尔雅尼乐团成员,致力于保持传统音乐在这一地区的活力。席间每一道菜之间有音乐助兴,而歌曲的主题不外乎爱情和友谊的颂赞和英勇克敌的欢庆。古拉米担任“塔玛达”,即祝酒者,这是格鲁吉亚宴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每一轮祝酒词都必须富于创意并且发自内心(否则便会引发宾客起哄),并且杯中的本地佳酿要一饮而尽。这样的待客礼节常常使宴会持续三个小时或更久。
白雪皑皑的大高加索山脚下,颇具牛仔风范的乡村里,我在阿拉威尔第教堂附近的纳帕雷利葡萄酒博物馆发现这里的葡萄酒酿造也别具一格。人们用陶土制作巨大的卵形双耳细颈瓶(称为奎乌丽),放在和房间一样大的炉中烧制后埋入幽暗的土中,接着将用脚踩碎的葡萄连同汁液一同注入其中充分发酵(经历这一过程后,即使是白葡萄酒也会呈玫瑰色)。
然而,历经8000年后的这一工艺正在迅速变化之中。一位曾经是外科医生的酿酒师艾克·格隆迪曾试图在工艺流程中使用化学手段,“我们发现有机生长更好,无需使用任何农药和人工肥料。”他解释说:“我们从开始便追求完美,而不是事后试图改正。”在化学添加剂无处不在的国际葡萄酒业内,这个宣言比表面上更加重要。格隆迪首次推出的“伦理合规”拉维纳尼葡萄酒——使用农民朋友种植的葡萄——已见诸伦敦数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酒水单。
在军队公路最后一段的之字形转弯处盘旋而上,我暗自庆幸司机勒万一直谨守着四旬斋节期,因为过了滑雪胜地古道里(Gudauri),海拔升至2400米后,映入眼帘的是撼人心魄的雪景。这里,冬天的温度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足以使瀑布结冰,使车里的柴油凝结。我们的目的地是卡茨贝基(Kazbegi)——徒步旅行,直升机高山滑雪和攀登的圣地。即使尚不能与采尔马特相媲美,这里,一家于2012年开业的精品酒店“Rooms”与第比利斯的同名姊妹酒店保持同样的舒适水准和时尚风格。热情友好,操一口流利英文的酒店职员,富于创意的烹饪艺术和时尚氛围与苏维埃时期被抽去灵魂的体系形成鲜明对比。
过了卡茨贝基,军队公路便在陡峭的峡谷间盘旋穿梭,直到与俄罗斯交界处,目前受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境线在原有基础上向南推进了数英里。按照惯例,为防止进一步入侵,格鲁吉亚人修建了一座新的大教堂。“我们信仰上帝——上帝,还有短剑。”考巴西泽微微一笑。世代居于山中的赫夫苏(Khevsur)武士们同意这一点。直到进入20世纪,他们还披挂着锁子甲,穿戴传统装束,手持传统武器在首都参加集会。年长的赫夫苏人素擅吟诗,买卖山羊时的讨价还价仿佛促膝长谈,连死亡威胁都因讲究押韵对仗而平添几分彻骨寒意。幸运的是,如今这些地区的血海世仇已经十分鲜见(砍下敌人的右手曾被视为传统习俗)。然而在这段眼界大开的日子之后,从高加索山脉和历史边缘返回第比利斯的我心中,古董级的海鸥牌汽车才是现代生活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