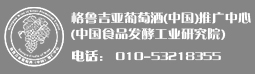作者: 发布时间:2017-10-05 关注度:179
拉玛兹与他的妻子很快就到了,从一片灰尘中驱车前来,卡尔特里 (Kartli) 地区典型的气候特征就是干燥。与众人道别,临行前我亲吻伊阿古的母亲,与她告别,虽然我知道我很快会再回来。我们一路向西,驶入更加潮湿温润的伊梅列季地区。
拉玛兹是Ghvino Underground葡萄酒俱乐部的骨干,因此,他需要长途往返于俱乐部与自己位于西部的葡萄园之间。他除了管理俱乐部,还着力寻找入行不久,且面容姣好的天然酒酿酒师,自己亲自培训,并让他们在店里施展才华。他家后院还保留着前苏联时期分配的自留地,在这里,他酿造大量不浸皮的骑士卡(Tsiska)葡萄酒,还有采用浸皮工艺酿制的索利格乌里(Tsolikuri)葡萄酒。
每次见到拉玛兹,我都很开心。上次是在卢瓦尔河布尔戈伊 (Bourgeuil) 的石灰岩溶洞外看见他,当时他身着格鲁吉亚传统羊毛斗篷,吸着卷烟,看起来就像《魔戒》里的人物。但是那一天,他却是一身夏季装束,头戴毛泽东时代典型的工人宽沿帽,穿着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Nul n'est cense ignorer la Loire,意为卢瓦尔河不容忽视。不要忽视卢瓦尔河?格鲁吉亚更不容忽视吧。
瑞克提 (Rikoti) 隧道直穿群山,贯通格鲁吉亚东部与西部。有人说,这是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唯一有价值的工程。整个旅程如同从干旱的西班牙中部一路飞驰,直达绿植如荫的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由于空气过于潮湿,我的头发变得有点卷曲。在这样的气候中,头发难以打理,而栽培葡萄更是不易。
我们前往阿奇尔(Archil)家,他是拉玛兹发现的一位酿酒师。一路上,我们看见农民在路边售卖水果和蔬菜,偶尔还能见到有人卖罕见的鸡油菌和凯撒蘑菇;我们还路过了几个主要卖甜面包或陶器的镇子。“阿奇尔的园子是什么样的?”我问拉玛兹。
“一会你就知道了。”
阿奇尔看起来像个数学系的学生,脸色有些苍白。但人不可貌相,要知道他可是位干体力活的农民。话不多说,他随即带我们穿过桑树下的小道,树上一个个珠串般的桑葚果垂下来,犹如小巧的圣诞装饰品。后面还有小块的农田。农民们都种葡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同一块田里种其他作物。阿奇尔打开园门,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的葡萄园。园子里的土壤呈芥末黄色,地里种着索利格乌里(Tsolikuri)和奥茨卡努利•萨佩丽(Otskhanuri Sapere)葡萄藤,同时他还套种了一些水果和蔬菜,供家人食用。一块土地却开发出这么多用途。
他跪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有点像发黄了的骨头的颜色,里面还嵌着大量贝壳状的物质。 “啊,”我说道,“难怪颜色这么奇特。”红色的陶土土壤混杂着白色和黄色的石灰质地的化石。石灰岩混合黏土是所有优质土壤的共同特征。比如在皮埃蒙特和勃艮第,这种土壤就是酿造上乘葡萄酒的关键元素。
那么这里也有上好的土壤吗?
我对此毫不怀疑。
这儿的氛围让人陶醉。我感受着空气中的芬芳,欣赏着秀美的山峦,倾听着周围的声音。在这里,昆虫与飞鸟齐鸣,葡萄、桃、梅子、杏子竞相生长,阳光明媚,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时值夏季,这里却保持着零度的凉爽。万物都平衡存在,维护着和谐的生态系统。我不禁想起酿酒师们辛苦钻研生物多样性,在葡萄园中套种其他作物,如草本植物、花、丁香树、三叶草。我想到人们想方设法拯救被毒害的土地。我觉得,那些总是将生物多样性挂在嘴边的人应该来格鲁吉亚看看。
人们热衷的生物动力法的灵感来源于自然顺势耕种法。人们膜拜生物动力法的鼻祖鲁道夫•斯坦纳 (Rudolf Steiner)。算了吧!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并有着我自己的理论:农业与弗洛伊德。我突然觉得弗洛伊德的著作—《文明与缺憾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与我的理论紧密相关,尤其是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对自由的本能追求与文明社会对同一性的要求是对立的。我认为,这同样可以应用到葡萄园以及格鲁吉亚当下的情况之中。
格鲁吉亚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樱桃树紧邻杏树,杏树的另一边则是桑椹树,旁边还种着石榴树,接着还有榅桲树。多种植物混种造就了复杂的果实口感。在美国,口味已被剔除,人们的味蕾似乎只习惯甜味。他们把苹果树隔离起来,集中种植,洋蓟和浆果也一样,全部分类种植。我怀疑回到美国之后,我还能忍受美国樱桃的味道吗?我能接受那单调乏味的口感吗?我敢肯定,我对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热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多样化的植物及土壤类型。我的内心顿时激动不已。
“怎么了?”拉玛兹问我,他又开始抽烟了。清新的空气到此为止。
“这里太美了。”我喃喃地说到。“这里的蜜蜂也不蜇人,它们是那么的快乐与满足。但我有一个担忧,一旦需求开始增长,你们购买更多的土地并扩大种植规模,耕种会变得碎片化,程序化,那时,葡萄园的多样性会不会消失呢?就像我整理书桌,我必须把桌上的文件分门别类地放起来,才不至于使书桌变得一片狼藉。然而在葡萄园里,有序的种植就意味着所谓的文明式的、碎片化耕种,园子里除了葡萄藤,别无他物。想想智利、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望无际的农田里,除了葡萄藤,还是葡萄藤。”
我双手比划着,“怎样才能做到在商业上成功的同时,仍然保持葡萄园里的自然和平衡呢?在有序化农业及葡萄栽培逐渐抹煞个性化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农业,难道不应该回归自然吗?”
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如此大规模的扩张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譬如,伊阿古确实想壮大规模。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葡萄酒产量已经增加了一倍,这足以养活其家人,他也可以全职酿酒,并且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些财富,但这并不足以使他征服整个葡萄酒世界。拉马兹只是想要谋生,他希望拥有足够的土地,将酿酒作为他唯一的事业。我打交道的当地人中,没有一个人有称霸葡萄酒世界的野心。
从第一天来到格鲁吉亚,我头一次感觉到饥饿,想吃东西了。在阿奇尔家狭窄的走廊里,我与他的孩子、父母和妻子共进午餐。
饺子捏得特别好,而且美味可口。我吃着香喷喷的饺子,而餐桌上的话题似乎有些凝重了。拉玛兹用他沙哑的嗓音,悄声对我说:“他们开始讨论前苏联时期丢失了多少葡萄品种。”
葡萄品种遗失是格鲁吉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在伊梅列季地区,葡萄酒复兴的势头还十分强劲。而拉恰地区的情况呢?那里可没这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