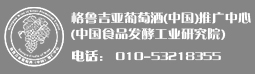作者: 发布时间:2017-08-29 关注度:221
无硫有机酿酒之风起源于法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名叫马赛尔•拉皮埃尔(Marcel Lapierre) 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们掀起了这场风潮。而在格鲁吉亚,引领葡萄酒革命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长者,至少是中年人。当盖拉找到约翰的时候,已经30岁了,虽然不算老人,但也不是小伙子了。这股酿酒工艺复兴的浪潮,正是由那些梦想被迫搁置的人们推动,他们的年龄介于30岁到70岁,勇敢推动着改革的步伐。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开创了振奋人心的葡萄酒新时代,推广有机酒,号召人们摒弃化学添加剂。可以说,这场反对化学添加、不走寻常路的葡萄酒革命是一场鲜有年轻人参与的战斗。
慢食组织 (Slow Food)成立于意大利,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地区特色烹饪方法与传统农业。该组织在格鲁吉亚设有分支机构。索立科与其负责人拉玛兹(Ramaz)见过面。拉玛兹身材健壮,颇有主见,声音有些沙哑,而且他也酿酒。两人价值观相似,一拍即合。他们随即开始四处网罗同样热衷传统工艺,能酿造优质天然有机酒,并愿意推动市场的人才。他们就像葡萄酒传教士一般,共同努力,最终将创建一个庞大的网络。
迪蒂米(Didimi)已年逾七十。老人家的肖像被印在酒标上,并注有“我是迪蒂米,这是我的卡胡娜葡萄酒”的字样。这款酒首次在意大利市场销售。还有一位老人叫盖奥兹•苏普奥马兹 (Gaioz Sopromadze) ,六十多岁,似乎由于过多食用khachapuri 芝士面包而挺着大肚腩。他用莎卡维拉 (Chavkeri) 葡萄酿出了如今非常受欢迎的酒。2013年,他首次去法国推广自己的葡萄酒。我在巴黎的一场品酒会上认识了他。那时的盖奥兹正沉溺于风姿绰约的巴黎美女之中。对此,他不以为然,辩解道:“她们实在太漂亮了!”。那周晚些时候,我与他在卢瓦尔河谷一间漂亮的酒窖里见面,在场的还有另外几位格鲁吉亚人。酒窖很深,储藏了不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好酒。盖奥兹当时有些愤愤不平:“我祖父曾有三公顷葡萄园。1921年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夺走了。”他非常激动,似乎这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他们瓜分我们的产业,抢走了我们的土地,分给了什么都不懂的人。他们掠夺我们的酒窖,里面收藏的好酒就跟这里的一样。”他冷笑着,继续说道:“我讨厌前苏联,讨厌苏联共产党。”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无论是纺丝工人还是酿酒师,他们渴望在自己的领域出人头地的梦想,被前苏联击得粉碎。而如今,一切都有实现的可能。老人们又重新充满激情。虽然盖奥兹只有0.75公顷土地,但他已经在着手购置新的葡萄园。他这把年纪了还要重新栽葡萄?葡萄藤几年都结不了果,这样的付出还有意义吗?这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乐观精神啊。而在格鲁吉亚,精神追求深植于人心,人们对长远梦想的奋斗也从未停止。
午餐的香味从索立科的房子里飘散出来,美食已经摆放在一棵樱桃树下的餐桌上。索立科的妻子尼诺加入我们,听着我们对她厨艺的夸赞。餐桌上摆着油炸馅饼、各式蘑菇等。还有一道鸡蛋做的美食,非常好吃,鸡蛋像是来自被施了魔法的母鸡。我们品尝着索立科的年份酒。这时,他举起 2006 年卡斯泰利葡萄酒,动情地说:“这是我的挚爱。这就是我。”
四个小时后,我们的人数增加到六个,午餐仍在继续。在格鲁吉亚,午餐很容易就被拖延到下一顿开餐。盘子逐渐堆积如山,已经盖满了白色的桌布,这也是当地的习俗。家里有客人时,每顿饭都是大餐,都是一场饕餮盛宴。尽管我已经撑得像头牛了,但也不能停下来喘口气。因为之后,另一位酿酒师又要带我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告别时,我倚着门框看索立科帮尼诺清理餐桌。他们一边忙活,一边唱着多声部歌曲,这旋律在其他国家从未听过。我突然意识到,多声部音乐不仅仅是像约翰妻子凯特温的Zedashe那样的艺术团所做的娱乐表演,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旋律与歌声层次分明,恰似极富层次感的葡萄酒。这种歌唱的艺术,以及万物多样化的理念,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卡哈•贝尔什维利 (Kakha Bershivili) 带我到他家。由于他完全不懂英语,便找来他女儿的朋友当翻译。卡哈是一位素食主义者,也是小提琴艺术家。他还尽可能地在葡萄园耕作,也酿葡萄酒。他坚定地支持天然酒,同时他也加入“青春虽逝,葡萄酒革命不老”的队伍中,复兴传统工艺。我们在特拉维市下车,拾级而下走进喧嚣的市场,找到菜摊,买了一公斤蘑菇以备晚餐用。
当晚,参观完卡哈的葡萄园和酒庄,并沿河边散步返回之后,大家便开始忙着做饭,在走廊喝酒。夜色渐浓,胡狼的嚎叫与青蛙,昆虫的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从未听过这么持久不息的虫鸣声。临近夏至,自然界一片生机。
谈话中,我逐渐对这个20 来岁的翻译产生了兴趣。他也是一位酿酒师,希望在学完酿酒专业后,能有机会去新西兰和勃艮第实习。
“你想去哪儿工作?”我问道。
他想在格鲁吉亚或其他国家的大酒厂谋一份职。
“真的吗?”我很惊讶,“但今天听了这些故事,喝着这些酒,难道你对这种特殊的酿酒技术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他笑了。他说,他也喜欢这种酒和它的口感,但他补充道:“这样酿酒太辛苦了。”
“辛苦?那些比你年长几十岁的前辈都没有抱怨,你怎么能喊累呢?他们都不怕累啊。”我说道。
这个年轻人生于前苏联解体之后,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他无法真切体会年少怀才不遇,中年方能施展拳脚的感受。想到这儿,我有些难过,我想到那天深夜我和尼基在第比利斯,与烹饪学校的那个家伙争论的情景,当时的感受与现在一样。清洗Qvevri陶罐的确很辛苦,但格鲁吉亚人还怕苦怕累吗?
“你就想多挣钱。”我责怪他,他温和地笑了。
我们喝着2009年的好酒和第一批2006年份酒,我问这年轻人:“你可以找一份大酒厂的工作,但是你酿造自己都不愿意喝的酒,晚上能安心睡觉吗?难道你不想像卡哈一样酿出好酒吗?”喝着新酒老酒,我们开始吃蘑菇。我吃着美味的西红柿餐,开始担忧格鲁吉亚的未来,如果年轻一代不愿像老一辈那样埋头苦干,那么工业生产会不会取代传统酿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无疑将是一场灾难。